來(lái)源: 時(shí)間:2023-01-12 14:05:04
中金網(wǎng)今日介紹"盛女的黃金時(shí)代劇情(盛女的黃金時(shí)代插曲叫什么名字)",希望小金從網(wǎng)上整理的盛女的黃金時(shí)代劇情(盛女的黃金時(shí)代插曲叫什么名字)對(duì)您幫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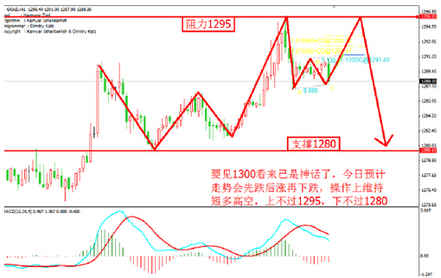
本文轉(zhuǎn)載自寧胡閼氏在公眾號(hào)的原創(chuàng)文章,已經(jīng)得到作者授權(quán)。
一、名節(jié)
話說(shuō):漢魏之士多重名節(jié),然而知名節(jié)卻不以禮法加以節(jié)制,遂至于苦節(jié)。故當(dāng)時(shí)名節(jié)之士,有視死如歸者。苦節(jié)發(fā)展到極致,就是魏晉之士的曠蕩,尚浮虛而亡禮法,此即為誕節(jié)(荒誕的名節(jié))。
這句話揭示了東漢—魏晉間,士風(fēng)轉(zhuǎn)變的過(guò)程及原因:名節(jié)之極而至苦節(jié)、苦節(jié)之極而至誕節(jié)。然而尚須追問(wèn)的是,名節(jié)為何要“至于苦節(jié)”,苦節(jié)又為何要趨于“極”,而變得荒誕呢?如果先說(shuō)結(jié)論的話,它與漢代的察舉制度有關(guān),這是漢魏士風(fēng)及其主體轉(zhuǎn)變的內(nèi)在原因。
自西漢武帝尊崇儒術(shù),特別是好儒的漢元帝之后,經(jīng)學(xué)大盛,儒生日多。漢成帝時(shí)太學(xué)生,增弟子員三千人。東漢光武帝愛(ài)好經(jīng)術(shù),明帝親臨太學(xué)典禮,至順帝時(shí),游學(xué)增盛,洛陽(yáng)的太學(xué)生多達(dá)至三萬(wàn)余人,占據(jù)洛陽(yáng)總?cè)丝诘氖种唬?guó)學(xué)生尚不在其內(nèi)。民間經(jīng)師開(kāi)私學(xué)授徒,“傳業(yè)者浸盛”,門(mén)生數(shù)量眾多,或“編牒(學(xué)生名冊(cè))不下萬(wàn)人”,如汝南蔡玄門(mén)下,“其著錄者萬(wàn)六千人”。
但是,儒生的出路只有學(xué)優(yōu)而仕一條,開(kāi)門(mén)授徒也不過(guò)是這一條道路的延伸。而東漢中后期,在太學(xué)乃至私學(xué)習(xí)業(yè)的儒生,總數(shù)以十萬(wàn)計(jì),都擠在入仕這一條獨(dú)木橋上,競(jìng)爭(zhēng)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見(jiàn),可謂“學(xué)者如牛毛,成者如麟角”。
東漢中后期又恰是宦官專權(quán)的時(shí)代。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,牧守令長(zhǎng)、布滿天下,占去大量職位,從而使士人向上流動(dòng)的通道變得更加狹窄,也使士大夫集團(tuán)與宦官勢(shì)力的矛盾更加激化,這也是黨錮事件發(fā)生的重要原因。
然而促使士風(fēng)改變的根本原因,還是士林內(nèi)部的競(jìng)爭(zhēng)。經(jīng)學(xué)之盛,漢代選舉以察舉為代表,察舉又以孝廉為主,秀才(茂才)次之。但不管哪一科,都需要通曉經(jīng)學(xué)才行。“通一藝以上”是儒生(諸生)入仕所必經(jīng)的考試,東漢順帝朝的“陽(yáng)嘉新制”,“通家法”即考試經(jīng)術(shù)始成為察舉孝廉一個(gè)必經(jīng)環(huán)節(jié)。
孝廉本為儒家倫理的實(shí)踐,故察舉孝廉的中心環(huán)節(jié)還是郡國(guó)舉薦,舉薦的重點(diǎn)則在德行,即孝悌與廉讓。總之,漢代選舉的主要標(biāo)準(zhǔn),按照當(dāng)時(shí)的術(shù)語(yǔ)就是“經(jīng)明行修”。“經(jīng)明”可以通過(guò)自己努力,其成績(jī)也便于考察。“行修”則取決于他人的觀察和評(píng)價(jià)。
因此宗族鄉(xiāng)黨的批評(píng),道德所施對(duì)象的評(píng)價(jià),也就是所謂“鄉(xiāng)里清議”、“鄉(xiāng)論”,就成為選舉上最重要的憑藉和標(biāo)準(zhǔn)。郡國(guó)對(duì)孝廉的舉薦,其根據(jù)就是被舉薦者在鄉(xiāng)黨的名望,可見(jiàn)“行修”要取得好的成績(jī),實(shí)取決于名望。
范曄在《后漢書(shū)》論“東漢之所謂名士者:“刻情修容”。所謂“刻情修容”就是矯揉造作以表現(xiàn)“行修”,以博取名望,高抬身價(jià)。通過(guò)不正當(dāng)?shù)氖侄尾┤∶@樣的名士并不能通達(dá)事理、應(yīng)付時(shí)需。
作為儒家倫理實(shí)踐的“行修”,具體體現(xiàn)為禮教或曰名教,包括小至言行舉止的中禮,大至對(duì)三綱五常的遵循。當(dāng)時(shí)太學(xué)諸生,有專門(mén)的服裝,要學(xué)習(xí)矩步。《儒林列傳》中的:沉靜樂(lè)道,舉動(dòng)都很講究禮。他的學(xué)生周燮:志行,非禮不動(dòng),對(duì)待自己的妻子像君臣那樣恭敬。
禮之大者莫過(guò)于喪禮,鑒于“生孝”難以考察,故服喪便成為孝的主要表現(xiàn)形式。在西漢成帝時(shí)代,少有依禮行三年喪者,但到兩漢之際特別是進(jìn)入東漢后,行三年喪的就多了起來(lái)。
漢光武帝時(shí)“雅稱儒宗”的韋彪,《后漢書(shū)》稱其:孝行純至,父母卒,哀毀三年,不出廬寑。守孝完畢,他整個(gè)人變得羸脊骨立異形,調(diào)養(yǎng)療愈了好多年才恢復(fù)健康。他后來(lái)“舉孝廉”可謂名副其實(shí)。至遲在安帝時(shí)行三年喪已普遍化,其后士人為了在“行修”上有異常表現(xiàn),于是有突破之舉。
漢安帝時(shí)汝南薛苞,“喪母,以至孝聞”,父及繼母死后,又“行六年服,喪過(guò)乎哀”;苞與其侄分家時(shí),奴婢只要老朽的,房子田產(chǎn)只要破敗的,東西只要破爛的。廉即讓,讓名讓財(cái),薛苞真是既孝且廉,后來(lái)拜官,“受祿致禮”,乃實(shí)至而名歸。
宗室東海王臻,以及袁紹都是服喪六年,因父死時(shí)年幼,長(zhǎng)大后又補(bǔ)服三年。又有為長(zhǎng)官、、恩師制服守喪者,為同僚、同窗千里奔喪者。讓爵讓財(cái)者,亦多不勝舉,如鄉(xiāng)侯鄧邯死后,其子鄧彪讓其爵位于異母弟鄧?guó)P,張禹父卒后,以田宅讓其伯父,韓棱以父財(cái)數(shù)百萬(wàn)讓給從弟韓昆。
以上都是對(duì)儒家喪禮和漢代法定爵位、財(cái)產(chǎn)繼承方式的突破。趙翼《廿二史札記》:“東漢尚名節(jié)”條將這種現(xiàn)象與當(dāng)時(shí)的選舉制度聯(lián)系起來(lái):當(dāng)時(shí)的察舉制,主要看重人的名譽(yù),所以只要有利于樹(shù)立名譽(yù)的事情,大家都爭(zhēng)相去做,標(biāo)榜自己,以致于形成攀比的風(fēng)氣。
其實(shí)東漢人應(yīng)劭《風(fēng)俗通義》中,就針對(duì)這類現(xiàn)象進(jìn)行批評(píng)。他指出,當(dāng)時(shí)有人在母親、兄弟死后不歸家服喪,卻為長(zhǎng)官、舉主服喪,難道“真不愛(ài)其親而愛(ài)他人”嗎?實(shí)因后者都是名門(mén),達(dá)官貴人,爭(zhēng)相獻(xiàn)殷勤和攀附,就是希望以后在仕途上得到奧援,在社會(huì)上獲得名譽(yù)。
當(dāng)時(shí)的士人認(rèn)為,雖然“過(guò)”了一些,儒家本強(qiáng)調(diào)中庸,“過(guò)猶不及”,但儒家又有“觀過(guò)知仁”之說(shuō),故還是寧左勿右保險(xiǎn),寧過(guò)而唯恐不及。對(duì)禮的突破既根源于要在“行修”上出奇制勝,以獲得作為察舉憑藉的名譽(yù),于是這種突破就有類于打破紀(jì)錄的體育競(jìng)賽,為破紀(jì)錄而百計(jì)千方,同時(shí)也一如體育競(jìng)賽,難免出現(xiàn)虛偽和作弊。
東漢服喪上的最高紀(jì)錄是桓帝時(shí)青州樂(lè)安郡人趙宣創(chuàng)造的。他“為父母服喪二十余年”,以墓道為居室,“鄉(xiāng)邑稱孝,州郡數(shù)禮請(qǐng)之”。郡太守陳蕃聽(tīng)到他的模范事跡后,親臨訪問(wèn),方知他在所謂的服喪期間,連續(xù)生育了五個(gè)子女,這是嚴(yán)重違反喪禮的行為,遂大怒而“致其罪”。
因?yàn)橐蓝Y服喪,衣食、住行、起居皆有嚴(yán)格規(guī)定,三年下來(lái),大抵如上舉韋彪,“羸脊骨立”,不成人樣,“醫(yī)療數(shù)年”才能康復(fù),死于服喪中的不乏其例。這是孝的作偽。據(jù)《后漢書(shū)·許荊》:許荊的祖父許武被舉為孝廉后,考慮到兩個(gè)弟弟還未出名,就“共割財(cái)產(chǎn)以為三分”,而“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(qiáng)者,二弟所得并悉劣少”,從而為兩個(gè)弟弟博得了“克讓”也就是“廉”的名聲,均被察舉為官。
若干年后,許武又召集“宗親”,哭訴當(dāng)年分家時(shí)自己多占財(cái)產(chǎn),是為了弟弟們的前途,并且又將自己業(yè)已增殖的財(cái)產(chǎn)“悉以推二弟,一無(wú)所留”。而此舉又為許武博得了更高的聲譽(yù),因?yàn)檫^(guò)去貪財(cái)是為了弟弟當(dāng)官,是“孝悌”,現(xiàn)在將財(cái)產(chǎn)送給弟弟,是“廉讓”,于是“遠(yuǎn)近稱之”,官升至“長(zhǎng)樂(lè)少府”。顯然,這兩次財(cái)產(chǎn)分割,都是有預(yù)謀的操作、炒作、矯揉造作,是廉的作偽,也是孝悌的作偽。
這種的社會(huì)風(fēng)氣發(fā)展到魏晉之際,則演變?yōu)檎Q節(jié)、曠蕩。
二、誕節(jié)
《風(fēng)俗通義》卷四《過(guò)譽(yù)》:
江夏太守河內(nèi)趙仲讓,舉司隸茂材,為高唐令。為郡功曹所選,頗有不用,因稱狂,亂首走出府門(mén)。太守以其宿有重名,忍而不罪。后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,冬月坐庭中,向日解衣裘捕虱,已,因傾臥,厥形悉表露。將軍夫人襄城君云:“不潔清,當(dāng)亟推問(wèn)。”將軍嘆曰:“是趙從事,絕高士也。”他事若此非一也。
《洪范》陳五事,以相貌為首;《孝經(jīng)》列三法,以服飾為先。衣冠、冠帶,本是儒家禮樂(lè)文明的象征,因而成為官吏、士人的代稱。東漢太學(xué)生的典型形象,就是“方領(lǐng)”、“長(zhǎng)裾”、“矩步”、“進(jìn)止必以禮”。
然而這個(gè)趙仲讓卻“亂首”“稱狂”,甚至于當(dāng)眾裸體,這是對(duì)當(dāng)時(shí)名節(jié)、苦節(jié)的反動(dòng),并開(kāi)魏晉名士劉伶、王澄、謝鯤、胡毋輔之、阮放、光逸等“散發(fā)裸裎”、“裸體”的先河。而且趙仲讓“宿有重名”,甚至連執(zhí)政梁冀都任其狂放,也許梁冀認(rèn)為,別人裸體自然是失禮,但對(duì)于“絕高士”的趙仲讓來(lái)說(shuō),不過(guò)是演繹其高情逸致的“行為藝術(shù)”而已。表明士林風(fēng)氣及評(píng)價(jià)標(biāo)準(zhǔn)正在悄然生變。
《后漢書(shū)·袁閎傳》:閎“少勵(lì)操行,苦身修節(jié)”。其父任彭城相,他在“省謁”的來(lái)往途中,包括在彭城郡界,“變名姓,徒行”,既不肯暴露郡相之子的身份,又不肯坐父親給他派的公車(chē)。后來(lái)其父死于任上,他去迎喪時(shí)“不受賻贈(zèng)”(按照當(dāng)時(shí)慣例是很大一筆錢(qián))。他還拒絕身居高官的叔父袁逢、袁隗的贈(zèng)饋。這是絕對(duì)的廉讓,到了不近人情的“苦節(jié)”地步。
袁閎在護(hù)父喪途中,“缞绖扶柩,冒犯寒露,體貌枯毀,手足血流,見(jiàn)者莫不傷之”,是一種恪遵喪禮到令人感動(dòng)的至孝。然而同樣的袁閎,當(dāng)后來(lái)黨錮之禍時(shí),袁閎卻不著冠服。“散發(fā)絕世”,“筑土室”自居。其母親死后,他竟不穿孝服、不設(shè)母親靈位,與他父親死時(shí)所表現(xiàn)出的至孝絕然不同。
東漢初年以來(lái),由三年之喪而六年而二十余年,以至服喪期間飲酒食肉,在喪禮上完成了由苦節(jié)向誕節(jié)的轉(zhuǎn)變。時(shí)人無(wú)法適應(yīng)諸如袁閎那樣的由“苦節(jié)”一轉(zhuǎn)而至“曠蕩”,故稱閎為“狂生”,認(rèn)為他精神錯(cuò)亂了。實(shí)際上這是由于袁閎對(duì)自己過(guò)去所堅(jiān)持的價(jià)值觀(名節(jié)、苦節(jié))也喪失了信心。這樣的“狂生”是特定時(shí)代的產(chǎn)物。
無(wú)獨(dú)有偶,比如列于《后漢書(shū)·獨(dú)行列傳》的向栩:喜讀《老子》、披頭散發(fā),不著士服,長(zhǎng)嘯(歇斯底里的大叫),以及當(dāng)官而不任事,這些都是之后魏晉名士的行事特征。而且這種變化不僅僅限于外表、行為。
《后漢書(shū)·逸民列傳·戴良》:
字叔鸞,汝南人也。少誕節(jié),母喜驢鳴,良常學(xué)之以?shī)蕵?lè)焉。及母卒,兄伯鸞居廬啜粥,非禮不行,良獨(dú)食肉飲酒,哀至乃哭,而二人俱有毀容。或問(wèn)良曰:“子之居喪,禮乎?”良曰:“然。禮所以制情佚也,情茍不佚,何禮之論。夫食旨不甘,故致毀容之實(shí),若味不存口,食之可也。”論者不能奪之。
此即為“誕節(jié)”,《漢書(shū)》卷四十《敘傳下》:“誕節(jié),言其放縱不拘也。”“任誕”,也就是“曠蕩”。
戴良之學(xué)驢叫以?shī)势淠福M不是與西晉名士孫楚,因王濟(jì)生前喜愛(ài)孫楚作驢叫,故在王濟(jì)的靈前,維妙維肖地作驢叫相似么?重要的是戴良母親過(guò)世后,其兄伯鸞仍恪守喪禮,戴良卻吃肉喝酒,而且悲傷起來(lái)就哭,于禮該哭時(shí)未必哭。這些都是嚴(yán)重的失禮,但他傷心憔悴(毀容)的程度卻絲毫不亞于他依禮守喪的哥哥。
更重要的是他不認(rèn)為自己失禮,其誕節(jié)行為自有其理論根據(jù)。他認(rèn)為喪禮是用以限制那些缺乏人倫孝思、邪情蕩佚者的,而他對(duì)母親的孝思和哀傷由衷自懷,雖飲酒食肉,也符合禮。因?yàn)閷?duì)他來(lái)說(shuō),酒肉吃在口里也是苦的,故身心憔悴。惟其如此,他可以超越禮的限制,包括飲食衣著方面的喪禮規(guī)定。
他直指禮的人倫本質(zhì),而不拘守甚至超越其外在形式,可視為嵇康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先聲。阮籍服母喪期間照舊飲酒食肉,葬母時(shí),蒸一頭大肥豬,飲酒二斗,然后臨訣,舉聲大哭,吐血數(shù)升,以致很久恢復(fù)不過(guò)來(lái)。實(shí)質(zhì)上也是注重對(duì)母親的天然孝思,而無(wú)視喪禮的繁文縟節(jié)。可以說(shuō),從理論到實(shí)踐,“誕節(jié)”的戴良已無(wú)異于爾后“任誕”的魏晉名士,倘與嵇康、阮籍同時(shí),他應(yīng)是《世說(shuō)新語(yǔ)》的合適人選,竹林也很可能不止七賢。
古書(shū)中談?wù)摑h魏社會(huì)風(fēng)氣,有所謂“名節(jié)而不知節(jié)之以禮,遂至于苦節(jié),苦節(jié)至極,則為誕節(jié)。”的說(shuō)法,主要在于經(jīng)學(xué)的興盛激化了儒生數(shù)量膨脹,而選舉資源有限之間的矛盾,加上宦官專權(quán),導(dǎo)致仕途競(jìng)爭(zhēng)白熱化,最終使察舉制度諸要素變質(zhì)、異化,使得當(dāng)時(shí)的士人們思想發(fā)生變態(tài)扭曲,人性壓抑,與當(dāng)初的目標(biāo)預(yù)設(shè)相悖,最終變成沽名釣譽(yù),標(biāo)新立異,從而走向崩壞。
今日中金網(wǎng)關(guān)于盛女的黃金時(shí)代劇情(盛女的黃金時(shí)代插曲叫什么名字)的介紹就到此。
聲明:文章僅代表原作者觀點(diǎn),不代表本站立場(chǎng);如有侵權(quán)、違規(guī),可直接反饋本站,我們將會(huì)作修改或刪除處理。
相關(guān)推薦
猜你喜歡